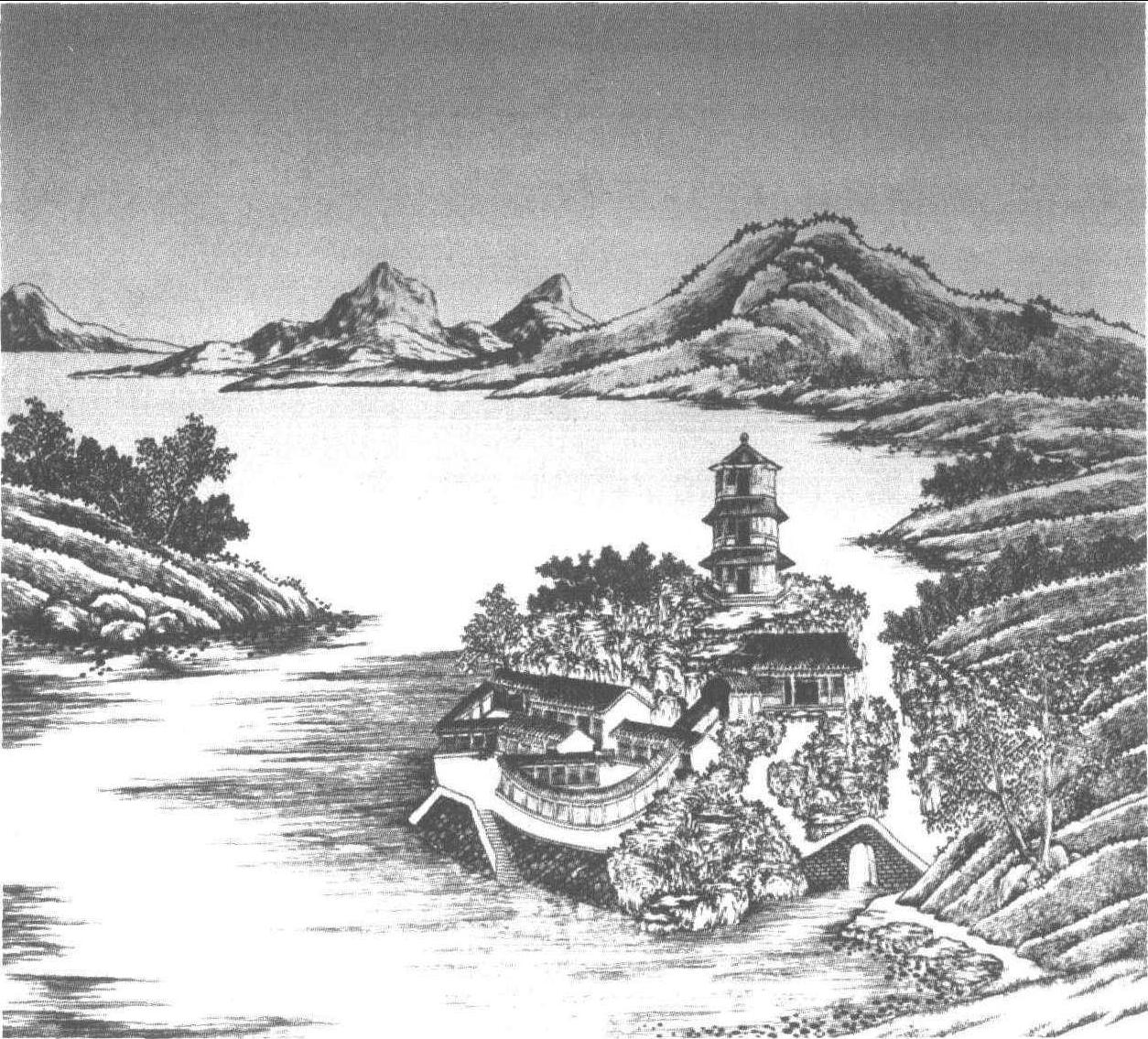
1839—1842年间的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的中国文化热的完蛋。——P.考纳这篇文章不是我的学术著作,是我从一本书上摘译下来的,有些地方稍加改写,有些地方作了些补缀。原书叫《东方建筑在西方》(OrientalArchitectureintheWest),作者是考 (本文共 19929 字 , 2 张图 ) [阅读本文] >>
海量资源,尽在掌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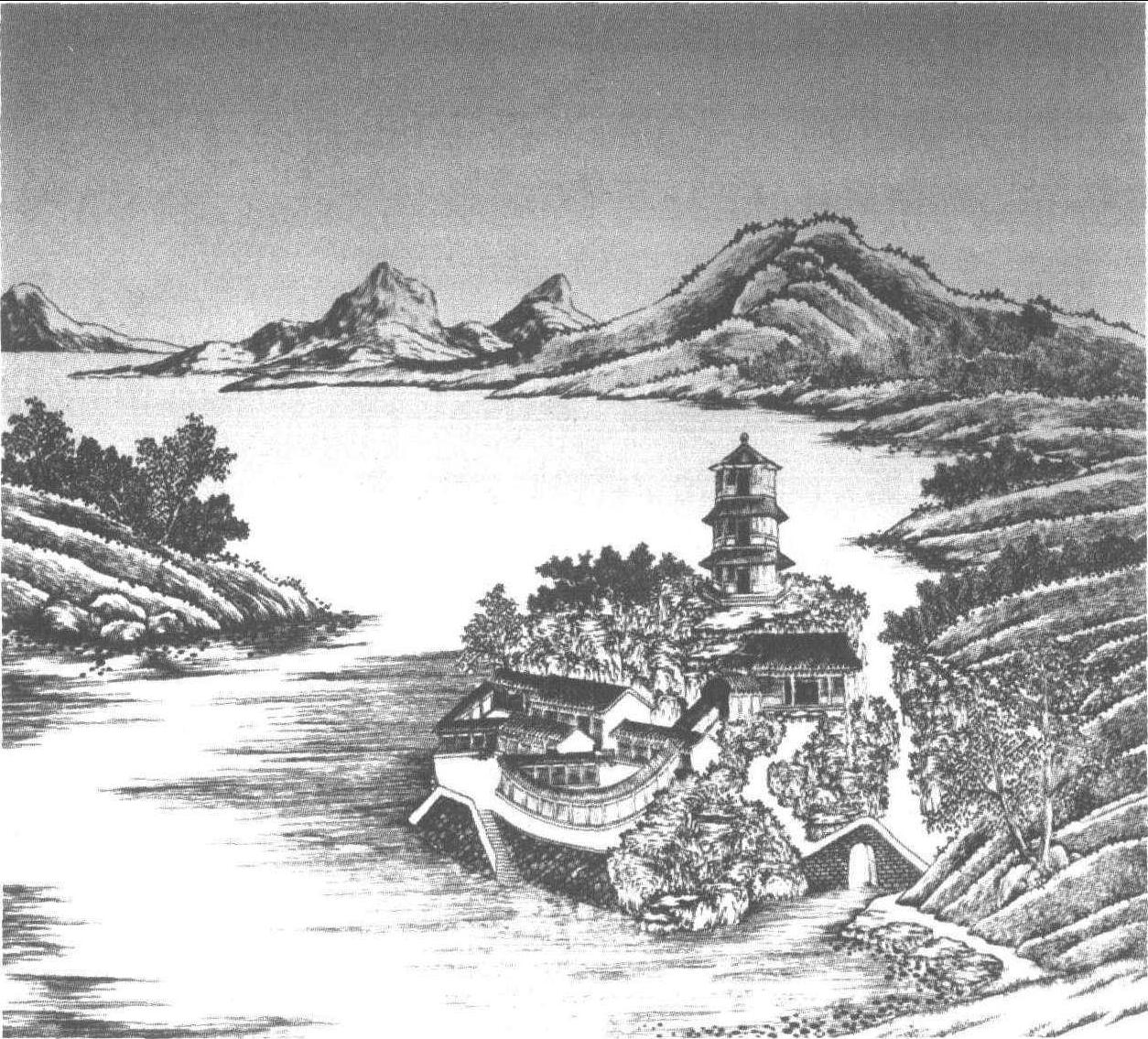
1839—1842年间的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的中国文化热的完蛋。——P.考纳这篇文章不是我的学术著作,是我从一本书上摘译下来的,有些地方稍加改写,有些地方作了些补缀。原书叫《东方建筑在西方》(OrientalArchitectureintheWest),作者是考 (本文共 19929 字 , 2 张图 ) [阅读本文] >>
 开通会员,享受整站包年服务
开通会员,享受整站包年服务